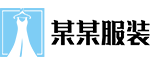今年五月第77届戛纳电影节选择了致敬日本电影天皇黑泽明在1991年上映的作品《八月狂想曲》,将其定格的一帧作为了今年戛纳电影节的官方主视觉海报。该片也曾于1991年入选了戛纳电影节的非竞赛展映单元。
《八月狂想曲》是黑泽明职业生涯末尾所产出的一部作品,他于1998年逝世,这是他所完成的倒数第二部作品。而把它放在以武士片闻名于世的黑泽明自己的漫长创作生涯中,它也是其中最不起眼的那一批影片之一。
影片故事讲述了一位住在日本长崎乡间的老人(伊崎充则饰),突然接到美国夏威夷的航空信。寄信人是老人的侄子克拉克(理查·基尔饰)。她得知哥哥早年移居美国而已成为富商,但现患不治之症,希望死前能与妹妹重聚。老人的儿女对突然出现有钱的亲戚兴奋不已,便把四个孩子寄放在老人家中,动身去了美国。孩子们在长崎逐渐了解了当年发生的历史。而听闻叔叔死于原爆的克拉克从美国回到长崎,他也亲身感受了历史的现场。突然美国来电告知老人的哥哥去世。克拉克匆匆离去。夜里,风雨交加,电闪雷鸣,老人踏着泥泞,向远处奔去,她以为这一天是1945年8月9日被投下那天。
这部毫无疑问直接聚焦于广岛长崎爆炸这段历史的影片,被今年戛纳电影节致敬而选为官方海报来源。今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评审团主席由美国导演格蕾塔·葛韦格担任,她也成为了首位担任这一职位的美国女导演。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是,继去年暑期“芭比海默”狂潮之后,格蕾塔在今年戛纳电影节又跟“”结下不解之缘!不知是不是戛纳的刻意为之?
说回影片本身,《八月狂想曲》不论在任何的维度上都称不上是一部足够好的影片。它在黑泽明的影迷心中地位不高,它也不是一个合格的探讨日本“原爆”历史问题的电影,它也甚至无意去真正地触及对于战争的反思。它像是黑泽明武士片的一个家庭情节剧版改写,塑造了一个来自于历史中的英雄,充满了黑泽明对于日本民族文化的乡愁,它同时还代表了黑泽明跻身世界影坛所依靠的民族寓言叙事策略。
如果上述评价不够明晰,那换个说法,观看完《八月狂想曲》,你会获得一种观看八十年代中国的伤痕电影的即视感,会惊呼和揣测,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和《归来》是不是对《八月狂想曲》有所借鉴?
但这可能不是过度的猜测,因为如果细看几部电影的叙事策略,你会发现很多相似之处。历史的家庭情节剧:用家庭代际间的矛盾冲突来表达历史的相关话题。在《八月狂想曲》中,黑泽明塑造了虚荣的、市侩的日本战后一代,他们听闻母亲远在美国有一位富商哥哥,便急于寻求投靠,而在长崎的四个孩子他们身着牛仔裤和短袖衫,衣服上印着“MIT”(麻省理工学院)、“USC”(南加州大学)、“New York”、“Brooklyn”等——极度直白地符号式地展现,他们是作为美国街头文化下成长的一代日本青年;而奶奶则一直穿着日式传统的服饰,与之形成了强调了对比;他们来到长崎,感叹道“这个美丽的长崎背后,还有另一个长崎在下消失了”,来到原爆的中心,那里建起了不同国家树立的纪念碑,他们若有所思。
其次,影片还借用了一个美国人(侄子克拉克)的眼睛,来认识长崎原爆,他带着深深的忏悔来到这里,因为这是他身为半个美国所人不可抹除的“原罪”。而后我们看见了这个家族的和解,四个孩子欣喜地迎接他的到来。而他怅然地游荡在长崎,在死于原爆的叔叔的房间里缅怀他。
一个外来者的眼睛能够帮助观众看见更多历史问题的侧面吗?还是说它只达成了遗忘和抛弃历史的效果。历史的问题被置换成了家庭内部的情感冲突问题,这是一种伤痕叙事的常用策略,集大成于谢晋,继承发扬光大于张艺谋。谢晋的《牧马人》甚至与《八月狂想曲》故事上异曲同工:一个早年出走美国而发家的中国人/日本人,多年后归来这个家庭,寻求和解。而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更是一种典型借助外来者之眼看本国历史,不必赘述。
这里便牵扯到黑泽明作为一个跻身世界影坛的日本导演,所依靠的民族寓言叙事策略。这个在自己生涯中多次改编了莎士比亚戏剧的导演(如《蜘蛛巢城》改编自《麦克白》;以及《白痴》改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名小说),在《八月狂想曲》中不厌其烦的使用舒伯特和贝多芬钢琴曲作为音乐。这或许是因为需要面向西方观众所作出的选择。的确,作为世界的电影大师,我们能够找到太多对他的学术性阐释,关于他电影中的“东方主义”的瑕疵;太多证据可以指控他的影片是一种美国理论家詹明信所称的“第三世界民族寓言”。
如果顺着这样的阐释角度去看《八月狂想曲》,我们会发现那个死于长崎核爆的爷爷,或许就是黑泽明一生追索的逝去的日本民族文化的具象化身。而奶奶则等同于黑泽明武士片中那些坚守原有日本价值的武士精神的化身。于是,《八月狂想曲》与其说是黑泽明在探讨广岛长崎核爆的历史问题,不如说他是用这个发生在长崎的家庭情节剧,重新伸张了他武士片中一贯追索的古典人文主义精神(正如黑泽明改编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当然就是西方人文主义的复兴)。奶奶这个坚守时代道德的平民英雄,与她的后辈的世俗腐化、迷失于物质世界的形象形成对抗。在影片的最后一幕,奶奶在电闪雷鸣之中,踏着泥泞,高举伞,如同黑暗中挥舞着旗帜,而风暴是猛烈的,她是一个悲剧性的英雄,又一个黑泽明书写的“卡里斯马”形象。
黑泽明电影中的武士,寄托了他对现代文明的精神遗失的反思,和他对世俗物质文明的质疑和抵抗。他们与经典好莱坞的西部片所塑造的牛仔,与中国武侠电影中的侠客,有所类似,都在各自文化跨向现代的过程中扮演着桥梁的作用。也难怪赛尔乔·莱昂内的《荒野大镖客》能够直接参考他的《用心棒》了(一桩影史公案)。
继续苛责地说,这个或许并无心探讨广岛长崎历史问题的家庭情节剧,在呈现历史的时候,事实上选择了回避历史,我们只能从奶奶口中听到她说“他们声称投下是为了停止战争,但45年已经过去了,人类的战争停止了吗?”这是显然是一句十分有力、意味深长的对历史的回应,但它只灵光一现,马上又消隐在随之而来的情节冲突之中。以至于到了电影后半部分,8月9日的核爆周年纪念日又快来临,长崎的人们进行着缅怀和悼念,在影片所呈现的一场场悼念仪式中,观众其实不知道应该去悼念什么,应该去向历史寻求一个什么答案,而只是着急地等待故事情节的下一次起伏。
一个有些唐突的联想是新海诚导演的《铃芽之旅》,一部关于日本“311地震”的电影。但影片中铃芽的冒险只是想一次次地关上门,阻止灾难的发生;她作为幸存者的记忆逐渐苏醒的过程,也是她不断地想要忘却灾难的过程——整个对于灾难的呈现,只是对灾难的“不见”和回避。正如《八月狂想曲》中对于广岛长崎的呈现,并非是对这场人祸的直视。
而一个不唐突的联想是法国导演阿伦·雷乃的《广岛之恋》,一个“讲述”广岛核爆的电影。这个极具现代先锋艺术观念的影片,近乎是使用了“非语言”/“反语言”的方式来呈现广岛。它用电影的方式生成了那句最直白的对于二战的哲思——“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那么多建立起来的纪念碑、博物馆,来留存人类的历史,而人类真正拥有了他们的历史了吗?
当然,也大可以不顺着这样的阐释去看《八月狂想曲》,那么你会得到一部夏日气息十足的日式乡间温情故事,或是感到略带疼痛,但又不知为何疼痛的悼亡仪式,以及一个家族跨越漫长时间、跨越国族的和解。还有一幕幕如同戛纳官方海报那一帧的,不乏愁绪的蓝色中,几人温馨的、佝偻的背影。就像我们能在《铃芽之旅》中获得的一幅幅唯美的色彩画卷一样。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